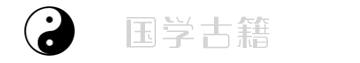大觉与大梦
我坐在车上等她们放生。
即便是清早,烈日夹着斑驳的树影晃得我眼花,我看着水塘边来来往往的人。
我看到有两种人,汗迹斑斑的男人和穿着清凉的女人。
我看到有三种人,奔跑喊叫的孩子、匆匆忙忙的青年人和拿着扇子和小板凳的蹒跚老人。
回到家之后我迫不及待的翻看了相册,看了孩子时期的自己,拿着糖葫芦的搞怪表情稚嫩懵懂;看着少年的自己,有青春期的倔强青涩,一直翻到现在。那些一张张脸庞是我吗?为何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甚至陌生大于熟悉。它们看起来每一张都不一样,也看不出哪里不一样,但是虽然只过去二十年罢了,陌生的像上一辈子。
我是如何从一个襁褓婴儿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中间是做了个梦吧?
其实这大街上来往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的缩影。当我们是孩子时,当我们是少年时,中年时和即将老年时。我看到拿着一把羽毛扇子的蹒跚走过的银发枯瘦的老人,看到那种步伐缓慢又摇晃的感觉一阵感慨心酸,可是几十年后我也会如此这般,但或许那时我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辛酸,也许我会觉得今天的微风甚好,极适合遛弯。我们彼此是一体的,我曾是你,你是曾是我,我即将是你……
也许我曾是男人,曾是女人,曾是一只蝴蝶,一只鸟。朝菌是我,惠跍是我,螟蛉是我,大椿是我。我们生生世世或者我们每个梦境都曾是万物。那些记忆不是在脑海里的,就如我记不清楚为什么二十年前的我为什么那么陌生又熟悉。那些做蝴蝶,做鱼的记忆是刻在DNA里的。在海里的时候会感到熟悉,在花丛中也感到喜悦,就当念到几百年前诗仙的一首诗,都能眼前浮现出画面。我看到天边的火烧云,好似跟几百年前或是梦里看到的一样美,我看到朝霞在云雾里透出的那种欢悦心情又似再次重拾。那种熟悉的感觉,是脑海里回忆不起来的,也许被刻在DNA里保留遗传下来我们曾是的每一种身份信息。
之所以今天想到这个是昨晚连续做了三个梦中梦。醒来发现是梦, 然后继续另外一个场景,又醒来发现还是梦,最后被闹钟吵醒,清晨的光才洒进了窗前。
那现在是个梦吗?也未可知。
每次午休的时候,我偶尔会做一个很冗长精彩的梦,醒来都会回味无穷,但是时间才过去不到十分钟,可梦里却度过了很久的欢乐时光。也许我们的梦在时间上是折叠的,那我们现在的一切未尝不是折叠在另一场梦中。
大觉才知其大梦。我们怀疑这人生是一场梦,但我们不确定,除非醒来的那一刻,阳光洒进来,新的故事又要发生。
可那新故事,是否是新的梦?
死亡也许是种大觉,也是醒来的一种方式,那一刻会发现无论编织多么春风得意或郁郁寡欢的梦顷刻就要化为泡影。那种就像是被闹钟强行叫醒的时刻,你不得不跳脱出来,哦,真是个糟糕(美丽)的梦。
在某个在普通不过的下班路上,我路过一个人,很熟悉。回头看他,他也莫名回头看我。脑海里搜索不到记忆,耸耸肩继续踏上回家的路。
梦中说梦,大抵就是最浪漫的不可解释吧。